原标题:重访
文章来源于网络,若有侵权,请联系我们删除。
三年之后,我又到了美国。这次的行程像是一次补遗,圆了一晤耶鲁这个梦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这次为期五周的“美丽修行”也时时呼应着三年前走过的路。
我在耶鲁修的其中一门课叫“现代主义文学”,上课的教授叫Nigel,他之前在耶鲁英文系任教。教授来自英国,操一口极其完美的英音,上课的时候老是无意识地把自己的眼镜摘下来再放回去。有一次课上他的左眼镜腿折断了,他的惯性动作如此根深蒂固,以至他把断了的眼镜架回了鼻梁上,直到它重新滑落前还不自知。
我忽然回想起三年前在自由之路上遇到的另一个英国人。他叫拜耳先生,是我们游览时的向导。过了这么久,我还能记得他在盛夏的天气里,拄着单拐,流着汗,以伦敦人的身份扮演数百年前英王的属臣,极其耐心地讲解一段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异国的历史。某种意义上,我的教授和拜耳先生是相似的,他们相似的地方不仅是国籍。彼时的单拐和此刻的单腿眼镜,似乎汇合成一个相同的隐喻,喻指一种对传递知识的纯粹热情。
我们从易卜生一直聊到奥登(我第一次听到奥登的名字还是在越读馆的课堂上),其中教授常常提起的一个概念是“互文性”(intertexuality)。我们在谈《都柏林人》的时候,就讨论到他其中的第二个故事“偶遇”是怎样促使读者回头重新打量第一个故事“姐妹们”中死去的老牧师的。而论及托马斯-曼的时候,我们注意到《死于威尼斯》深受尼采哲学影响,若不将其理论纳入分析范畴,阿申巴赫的故事会顿失一层意涵。如果把我的两次美国之行当作是两个并行的文本,它们其间的联系也是“互文性”的一种绝佳体现了。
我们那天刚刚学完《变形记》,回宿舍就看见郭老师在朋友圈分享越读馆学弟学妹们仿写的卡夫卡。小朋友们的想象力让我自愧弗如!阅读他/她们的文字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,格里高尔的悲剧命运是否会因为他变作的动物不同而发生改变呢?如果他变成了刺猬或是兔子,他还会落得一个背上嵌着一个腐坏的苹果,在自己家中死去的结局么?人与人之间滋长出的各种形状的感情,难道全都建立在同宗的前提上么?
如果说三年后重访美国有什么不同的体验,我觉得自己似乎更加难于惊奇而更加容易感怀。当时的我们走过自由之路,而现在我得以切切实实地接触到为自由作出努力的人。心理学里有个叫做情景依赖记忆(state-dependentmemory)的概念,再次得以浸入一个开放而包容的社群之中,我也借此召回了一些流散已久的记忆片段,从而不留情面地检视自己的变化。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,不也是充满“互文性”的两个故事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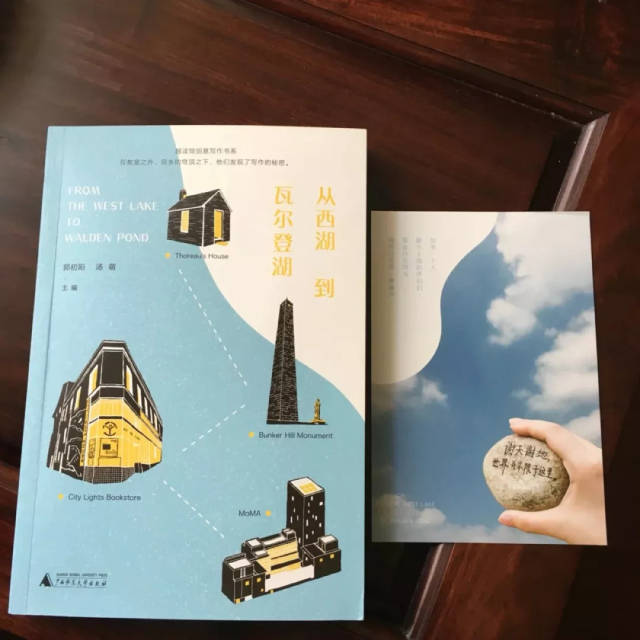
重游旧地作文(网络配图 侵删)
补:7月27日我搭乘大巴到波士顿去看我最爱的乐队之一ArcticMonkeys(北极猴)的演唱会。大巴在波士顿南站把我放下,我除了信任谷歌地图之外也别无他法,一路急行军赶去TDGarden体育馆,不想经过了当年走过的路:波士顿大屠杀的纪念遗址,那条再熟悉不过的红砖道---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涉足!继续往前走,法维尔集市就跟我隔街相望。我刹那间有点出神,我看着对岸熙熙攘攘的人群,好像能看到当时和拜耳先生作别的我们,又好像隔着更长的时间,看到对街的自己在兴致冲冲地背着初一刚入学时英文课本(AmericanEnglishinMind!)里面那篇关于波士顿的短文。(感觉自己身处《神秘博士》之中啊!)
我觉得自己像伊夫林-沃笔下重访故园的查尔斯。不同的地方在于,他说“爱”这个概念对他来说已经死了(Loveisdeadbetweenmeandthearmy.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!),而对于我来说,我才刚刚学会爱呢。而正在这个街口,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存在。我是快乐的。
2018.8.23



,2室2厅二手房出售,价格:52万元.jpg)




